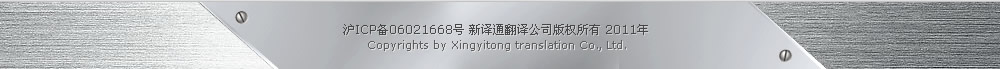当前位置:翻译公司|
当前位置:翻译公司| 上海翻译公司|
上海翻译公司| 北京翻译公司
北京翻译公司 >国际证明翻译>关于我们>翻译服务
英语翻译
日语翻译
>国际证明翻译>关于我们>翻译服务
英语翻译
日语翻译
专业 >信息技术翻译

关于我们 翻译服务 联系我们 翻译公司
专业信息技术翻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翻译服务提供商----新译通翻译公司设北京翻译公司和上海翻译公司提供英语翻译 日语翻译
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公司介绍:
信息技术公司人员大多毕业于国内外著名高校,并在信息技术公司领域有丰富的翻译经验。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在中外互译工作中,要求对两国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专业术语等有更加深入的把握,这样才能保证翻译的质量,达到及时、准确、规范的要求
, 我公司是一家专业信息技术公司
,在多种领域有丰富的学术翻译经验。我们翻译公司翻译人员都经过严格测试,大多有国外留学和工作的经历,都具有良好的翻译能力。
信息技术公司项目组成员对翻译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专业术语等都有深入的把握。为每位翻译客户提供高质量、快速度的翻译及服务。凭借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规范化的运作流程和独特的审核标准已为各组织机构及来自全球的公司提供了高水准的翻译,较多的公司还签定了长期合作协议。
什么是信息技术
哲学中关于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研究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影响也日益广泛。它一方面使传统的哲学问题获得新生,另一方面又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一方面对我们世界观重新概念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又生成许多有意义且重要的成果。最近,这个新领域又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有的追赶时髦的术语(例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计算机哲学”),而大多数则表达了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计算哲学”“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与哲学”、“计算与哲学”。本文则认为,最令人满意的名称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简称PI),其理由在第五节详细讨论。本文第二、三、四诸节则分析导致信息哲学问世的历史与概念过程。其结果支持以下两个结论:第一,人工智能哲学是不成熟的范式,但它却为信息哲学的问世铺平了道路。第二,信息哲学在概念创新和正统哲学之间达到了一种辨证。第五节介绍和探讨了信息哲学的定义。第六节总结了本文的主要成果并指出,信息哲学被解释为新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如何成为可能,尽管不是从一种常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视角出发。本文的所要辩护的观点:信息哲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因为(a)它代表了一个独立的领域(独特的话题); (b)它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手段(原创性的方法论); (c)它能够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
2、人工智能哲学是信息哲学不成熟的范式
纪德(Andre Gide)曾写道,发现新大陆要以很长时间见不到海岸为代价。为了寻找新大陆,斯洛曼(Aaron Sloman)1978年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在他恰如其分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这部著作中,他的猜测有以下两点:
1、 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
2、 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
然而,他的预测结果并不精确而且过于乐观,但却远非没有道理。
斯洛曼并非孤军奋战。其他研究者曾正确地察觉到,由信息与计算科学(ICS)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引起的实践与概念的转换,正导致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发生在科学,而且也发生在哲学领域。这便是所谓的“计算机革命”或“信息转向”。然而,与斯洛曼一样,他们似乎也被这场变革的特殊性质所误导,而且他们也低估了接受新的信息哲学范式所要遇到的不可逾越的困难。图灵(Alan Turing)于1930年代便开始发表他的那些开创性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控制论、信息论、人工智能、系统论、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还是相继吸引了一些来自哲学界的重要注意力(尽管它们是间歇性的),尤其是关系到人工智能哲学更是如此。因此,它们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和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方法奠定了基础。然而,直到1980年代之前,它们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更不用说1970年代那些像斯洛曼那样的研究者所预见的重大的革命性变革了。从后见之明的角度,很容易见到人工智能如何被视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新的研究领域,以及它如何成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一种根本性的创新方法。
自从图灵那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以及195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问世以来,在计算科学家当中,人们对心智理论概括具有相当大的兴趣。与此同时,在哲学家之中也有一种与日俱增的意识,计算机的出现已经(通过提出新的需要考虑的理论立场,至少是反驳的立场)决定性地改变了哲学的论辩。
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像特洛伊木马,把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计算机的与信息的范式引入哲学的城堡。然而,直到1980年代中期,信息哲学依然不成熟而且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无论这么说,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没有准备妥当。因此每种因素都需要简述一下。
与其他智力事业一样,信息哲学与三种领域相关:话题(事实、数据、问题、现象、观察等);方法(技巧、手段等);理论(假说,解释等)。一个学科若想在上述一个领域以上同时进行创新,则属不成熟,因为这样做便使之与一般领域的常规和连续演化的线索突然断离。看一下斯洛曼所作的那两点预测便可证明,这一问题恰恰发生在信息哲学作为人工智能哲学的早期形态。
信息哲学不可避免的交叉科学性进一步阻碍了人们对其意义的及时承认的前景。即便是现在,许多哲学家仍满足于考虑信息哲学所讨论的话题,仅仅是值得引起英语系、大众传媒系、文化研究系、计算科学系或社会学系(就举这几例吧)的研究者所注意的。信息哲学需要习惯于就跨越文化与科学边界的问题进行对话的哲学家,而寻找这类哲学家并不容易。常常是这样,人人都关心的恰恰是无人问津的行业,直到信息社会的最近发展之前,信息哲学被视为处于多个十字路口,其中即有技术事宜的,也有理论问题的,还有应用问题的以及属于任何人自己专业领域概念分析的等等。信息哲学被认为是跨学科的,就像控制论或符号学那样,而非交叉科学的,像生物化学或认知科学。我们以后还要回到这个话题。
即便信息哲学不是那样的不成熟或不是如此具有所谓的跨学科性,哲学界和科学界基本尚未对其重要意义做好评价的准备。尤其在语言哲学(逻辑实证论者、分析哲学家、常识哲学家、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解释学家、实用主义者)中,有各种各样的强研究纲领,它们一方面吸引了大多数的智力和财力资源,另一方面则保持一种相当具有刚性的议事日程并几乎不去促进可供选择的范式演变。主流哲学不可能不是保守的,这不仅是因为价值和标准在哲学中通常要比在科学中更不稳定和更不明晰,因此对其构成挑战也就愈发困难,而且是因为(正如我们在第四节将更详细讨论的那样)取得文化上占强势地位的背景常常是以牺牲创新性或非常规方法为代价的。因此,像丘奇(Church)、香农(Shannon)、司马贺(Simon)、图灵、冯·诺依曼(Von Neumann)或维纳(Wiener)这样的思想家,基本上均被遗弃在传统教规的边缘。不得不承认,计算机转向对科学的影响来得更迅速。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具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均是首批察觉到新范式涌现的人。尽管如此,斯洛曼的“计算机革命”还是要等到1980年代才成为一种跨越各门科学和社会背景的更为广泛和普及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为信息哲学的演变创造出正确的环境。
建造成首批大型计算机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在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涉及创造、动力学、管理以及信息和计算机资源利用诸问题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先进社会和西方文化还是要经历一场数字通信革命,才能完全意识到新范式的根本新颖性所在。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曝露在如此异乎寻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全方位渗透、灵活性以及强大的力量已经使信息与通信技术上升到具有时代特征技术的地位,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修辞上,甚至在意符上均是如此。计算机将其自身呈现为一种在文化上得到定义的技术,并且成为新千年的一种象征,它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远远超出中世纪的磨房、17世纪的机械钟表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织布机和蒸气机。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其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当下最具战略意义的因素。毫不夸张地说,最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是靠信息过活的,而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便是使之不断增氧的机器。然而,所有这些深奥的和非常有意义的转变在20年前几乎还看不到苗头,那时大多数哲学系会认为信息哲学所谈论的话题对研究生而言是不恰当的专业领域。
由于过于超前,而且其创新对大多数职业哲学家过于大胆,所以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可供选择的领域之间摇摆不定。它一方面生成许多有意义但又有限的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和计算机伦理学——常常与其知识背景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收,后来人们意识到信息哲学是一种计算机的和信息的理论方法,它不同于诸如认识论、逻辑学、存在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或心智哲学等传统话题。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涌现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3、信息哲学涌现的历史背景
人们常说,思想是“缥缈”的。这句成语的真正含义大概是这样的,在任何学科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思想看似成型,但只有眼光非常敏锐的人才能捕捉到。而在这个阶段之前,哪怕是思维最敏锐的人也察觉不到。
空想家的日子过得挺艰难。如若没人追随,他们就不会发现新大陆,在那些裹足不前, 仍住在洞穴里的人的心目中他们不过是走丢了。第三次与计算机相关的革命(因特网)要求全新的一代具有计算机修养的学生、教师和研究者,社会组织实实在在的变化,文化和知识界的根本变革以及哲学圈各个方向存在的普遍危机,所有这些因素均呼唤着新范式的涌现。到了1980年代末,信息哲学终于开始得到承认,认为它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创新的领域,并非一场不成熟的革命。也许有必要回想几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82年,《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将个人计算机评为“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APA)创立了哲学与计算机委员会(PAC)。同年,拜纳姆(Terrell Ward Bynum)——《元哲学》(Metaphilosophy)的主编——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Computers and Ethics)的专号(Bynum 1985),这期杂志“迅速成为在该杂志历史上卖得最火的一期”(Bynum 2000,亦见Bynum 1998)。首次由计算与哲学(CAP)协会出资赞助的年会于1986年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
其日程大都致力于逻辑软件的技术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CAP年会的主题已涵盖计算与哲学的所有方面。1993年,卡耐基梅隆大学成为东道主(自CAP网站)。
到了1980年代中期,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信息哲学不再被视为怪诞、难解、跨学科或与哲学不相关的了。像算法、自动控制、信息、反馈或符号表象等概念或过程;像人机互动(HCI)、计算机为中介的通信(CMC)、计算机犯罪、电子社区或数字艺术等现象;像人工智能或信息论这样的学科;像人工助理的本质、虚拟环境中个人身份的定义以及虚拟实在的本质等问题;像由图灵机所提供的模式、人工神经网络以及人工生命系统等……这些仅仅是在日益增长的话题中任选出的几个例子,这些话题越来越被视为新的、具有紧迫意义的和学术上可接受的。信息的和计算机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hermeneutic devices)的隐喻,通过它便可解释世界。它们已经形成一种元科学(metadisciplinary),具有统一的语言,这种语言已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
1998年,《数字凤凰》(The Digital Phoenix)出版了,这部文集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幅标题《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拜纳姆和摩尔(James H. Moor)承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情景中的一股新生力量:
哲学领域不时会发生一些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始于若干简单但却非常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为哲学家提供了审视哲学问题的新透镜。渐渐地,哲学方法和问题得到了提炼并根据这些新观念获得理解。随着新颖而有意义的哲学成果的获得,运动发展成一股蔓延至整个学科的知识浪潮。一个新的哲学范式涌现了[……]计算机的计算便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新颖而又演变着的为哲学探究所准备的主题、方法和模式。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
从教科书设定的距离上看,哲学是一个充满无休止的责难和各种异乎寻常主张的学科,就好像处于长期危机状态似的,这对学生是个打击。表象永远是这样,事实上,责难在思想强有力的动力中展开,主张则要求必要的深度,恰当的辩护水准以及它们全部的意义,而所谓的危机证明是在创新与正统哲学之间的一种颇有成效和不可避免的辨证。由拜纳姆和摩尔所强调的这种反思的辨证,在把信息哲学建设成一种成熟的哲学研究领域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历史的一面。这便是它何以在概念上得到解释的。
4、反思的辨证与信息哲学的涌现
要想达到涌现和繁荣的目的,思想需要通过不断地赋予数据以意义来使它所处的环境有意义。因此,精神生活便是对原始语义空虚恐惧(horror vacui semantici)的成功反动:无意义(用非存在论者的话便是“尚未有意义”)的混沌威胁着要把自我撕成碎片,要把它淹死在自我视为虚无的异化的他者的深渊,而这种原初的湮灭恐惧则迫使自我不断将任何语义为空的空间填充上自我所能聚拢起来的任何意义,其成功程度与背景约束,数据以及文化发展所允许的一样。这种存在的语义化过程,或者说自我对非我(non-Self,用费希特的话)的反动,存在于事实叙事(个人认同、日常经验、社区特质、家庭价值、科学理论、常识信念等)的传承和进一步的阐述,维系以及提炼之中,这些东西在逻辑上和背景上(有时完全)受限于各种数据,同时也受到各种数据的挑战,所以它们需要适应这种状况并得到解释。历史地看,这一过程的演变在观念上导向一种日益变化的、更加丰富和健全的世界架构。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它是四种概念挤压的结果:
1、叙事的元语义化(metasemanticisation)。对新的个体自我(他同样也需要相应的叙事)被外化为实在后所做的任何反动的结果,现在认为是自我被迫语义化的进一步的数据。反映转向反思并意识到自身就是需要解释和有意义的实在的组成部分。
2、文化的去界限化(de-limitation)。这便是外化以及分享由自我设计的概念叙事的过程。有意义的经验世界从一个私人的、主体内的和人类中心论的建构转移到一个越来越是主体间的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实在。话语团体通过维系、改善和传播一种语言(孩子学习语言就像遇难者拼命抓住一块漂浮的船板似的那样迅速)——及其概念的和文化的内涵——而分享使世界有意义所需的宝贵的语义资源。叙事因此变得愈来愈友善,这是因为与其他非挑战性的自我分享而非消除疑虑距一个自我的距离并不远,因为友善的叙事也是从某个未知的神灵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特殊叙事的生产消费者(produmers)不再受制于空间或时间,社区的成员由一组明显的跨越物理(trans-physical)空间的人员组成,事实上,他们在功能上由其愿意并选择居住的语义空间定义。全球化的现象更是一种消除旧有界限和创造新边界的现象,因此是一种文化去界限化的现象。
3、自然的去物理化(de-physicalisation)。物理世界充满监视和刀剑、石头和树木、汽车和雨水以及作为社会认同(性别、工作、驾照和婚姻状况)的我,但是这样的物理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虚拟化和疏远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即便是最基本的工具、最戏剧性的经验或最动人的情感——从爱情到战争、从死亡到性——均可以装入虚拟中介的框架,因此也就获得了信息的光环。艺术、商品、娱乐、新闻和他我均被置于一面玻璃镜后面,被人体验。在虚拟框架的另一方面,物体与个体完全是可以替换的并常常成为绝对无法区别的理想类型的标记:手表实际上就是思沃奇(swatch,瑞士手表的商标名),一支钢笔只有是名牌时才够得上礼品,一处地点被视为度假地,一间庙宇变成历史遗址,某人是警官,而一个朋友可以仅仅是存储在微机上的声音。个体实体被当成可以任意处理的特例。此处和当下的含义被改变了、扩展了。通过快速的多任务运行,个体的自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存身,甚至自我均体会到被同步感知的方式,因此,自我可以穿行在不同的生活中,它们没有必要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根据当下的时间被重塑为离散和多变的间隔。当前各种事件的各种投射和难以分辨的重复将其自身扩展到未来;未来事件在可以?
4、心灵设计和寄居的概念环境人格化(hypostatization)(具体化)。叙事(包括价值、思想、时尚、情感和具有意向性优势的宏大叙事的我)能够被塑造和外化为“语义客体”(semantic object)或“信息实体”(information entity),现在距离交互中的自我们愈来愈近,它们无声息地要求一种存在论的身份,可以与诸如衣服、汽车和房子那样的寻常物件相比较。通过去物理化的性质和具体化的叙事,物理的与文化的在虚拟世界中比肩并立。根据这种辨证,信息社会可被视为最近的——尽管不是最后的——更为广泛的语义过程的阶段,其中精神世界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该环境如若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的环境的话。作为人类行为结果的历史与文化,因此也就是时间,被推向前台,同时自然,即物理空间,则被推向没有人情味的后台。在它演化的进路中,语义化的过程逐渐形成建构的实在概念化,其结果便是确立时间性的世界观,然后生成一种保守的闭环——正统哲学。
正统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知识类型学而不是一种学术范畴,它所代表的如果不是对创新普遍的抵制时,就是概念体系与生俱来的惰性。最糟糕的是它是制度化的哲学(institutionalized philosophy),即社会语言学家称之为堕落的哲学家团体或小集团的内部“话语”。这种哲学将其自身展现为迂腐而且常常是偏执地依附于某种话语(教义、方法、价值、观点、作者的教诲、立场、理论或对问题的选择等),这种话语由某一特定的集团(哲学家、学派、运动、思潮)所设定,它以牺牲其他选择为代价,这些选择被作为异类而遭到忽视和反对。它尽可能永久性地和客观地确立一种哲学概念和语汇的工具箱,使之适合于它的话语的标准(它特殊的主义)和该团体的研究日程。如此一来,正统哲学则偏爱哲学的职业化:学究厌恶业余的想法,他们热衷于成为职业人士。他们把自己称为带后缀-an的“学者”,并将-an这个后缀置于其他哲学家的姓氏之后,不论是Aristotelians、Cartesians、Kantians、Nietzscheans、 Wittgensteinians、Heideggerians还是Fregeans。某个被神秘化的创始人的追随者、注视者和模仿者,这些正统学者手中现成的答案比新的有意思的问题要多,因此他们逐渐地将某些教义应用到解决内部的难?
不应将上述话题与诸如哲学是否迷失方向之类的幼稚的问题混淆起来,因此应该重新振作并与人们进行接触。人们可能会对哲学感到好奇,但是只有哲学家能够想象他们可以忘情其中。正统哲学如果得以适当的平凡化,还是能够走进大众的——“平凡” 毕竟会提醒人们对职业的热爱——而创新的哲学能够容忍晦涩。也许一个隐喻会有助于澄清这一点。概念领域就像矿山。有的矿山太大了,值得开采的内容太丰富,以至几代哲学家都乐此不疲,忘情其中。另一些矿山也许表面上看是被采空了,但是如果采用新的而又有力的方法或理论就会使之得到进一步和更深层次的开掘,或导致发现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先前所忽视的思想。正统哲学家就像在一座几乎被采空而又尚未遗弃的矿山采掘的可怜矿工。他们属于迟到的一代,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只允许他们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工作,只有在自己的领域内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工作努力但所获甚微,他们越是向贫瘠的研究投资,越是顽固地将自己埋在自己矿山之中,拒绝离开转向新的采掘地。悲惨的是,只有时间能够判定这座矿山是否真的开采殆尽。正统哲学只有死后才能得到谴责。
创新总是可能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正统哲学是必然的。存在语义化的任何阶段一开始如果不是破坏性的必定是创新性的,其目的是确立一种特殊的主导范式,因此势必走向不变而且愈来愈具刚性,进一步还要使这种态势得到强化,最终它会面临一场具备替代性的概念创新的挑战,它无法处理由它帮助确立的但却日益变化的知识环境。在这种意义下,每个知识运动均为自己生成了衰老和更替的条件。概念转换不应太彻底,以避免不成熟。我们已经见到过旧有的范式受到挑战和最终被进一步的创新反思所替代的情形,只有当新范式足够强健,被承认是对存在语义化中先前阶段的一个更好的和更可行的选择,这种情况才会发生。石里克(Moritz Schlick)曾就范式转移的开始阐释过这一辨证关系:
专业 >信息技术翻译
专业信息技术翻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翻译服务提供商----新译通翻译公司设北京翻译公司和上海翻译公司提供英语翻译 日语翻译
|
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公司介绍: 信息技术公司人员大多毕业于国内外著名高校,并在信息技术公司领域有丰富的翻译经验。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在中外互译工作中,要求对两国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专业术语等有更加深入的把握,这样才能保证翻译的质量,达到及时、准确、规范的要求 , 我公司是一家专业信息技术公司 ,在多种领域有丰富的学术翻译经验。我们翻译公司翻译人员都经过严格测试,大多有国外留学和工作的经历,都具有良好的翻译能力。 信息技术公司项目组成员对翻译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专业术语等都有深入的把握。为每位翻译客户提供高质量、快速度的翻译及服务。凭借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规范化的运作流程和独特的审核标准已为各组织机构及来自全球的公司提供了高水准的翻译,较多的公司还签定了长期合作协议。 什么是信息技术 哲学中关于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研究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影响也日益广泛。它一方面使传统的哲学问题获得新生,另一方面又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一方面对我们世界观重新概念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又生成许多有意义且重要的成果。最近,这个新领域又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有的追赶时髦的术语(例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计算机哲学”),而大多数则表达了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计算哲学”“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与哲学”、“计算与哲学”。本文则认为,最令人满意的名称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简称PI),其理由在第五节详细讨论。本文第二、三、四诸节则分析导致信息哲学问世的历史与概念过程。其结果支持以下两个结论:第一,人工智能哲学是不成熟的范式,但它却为信息哲学的问世铺平了道路。第二,信息哲学在概念创新和正统哲学之间达到了一种辨证。第五节介绍和探讨了信息哲学的定义。第六节总结了本文的主要成果并指出,信息哲学被解释为新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如何成为可能,尽管不是从一种常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视角出发。本文的所要辩护的观点:信息哲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因为(a)它代表了一个独立的领域(独特的话题); (b)它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手段(原创性的方法论); (c)它能够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
|